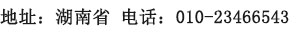关于电影《美国往事》的一点往事
作者:豆苇杭
纽约中央车站,三十五年的时间,仅是一扇门合、一扇门开,诺德斯鬓发霜白,回到故地,影片此时响起保罗·麦卡特尼的《昨日》,旋律刚刚开始,又戛然而止,只有隐约的“yesterday……suddenly“。
诺德斯神态依旧机警,步态却已蹒跚,环顾四周,如果说门合上前,是垓下之围,现在门开以后,未见故人,未能复曰:“吾闻汉购我头千金,邑万户,吾为若德。”
从暗道离开庄园,诺德斯似乎已得到所有的答案或解释,如来时路,他仍是踽踽独行,孑然一身,似乎没有过朋友,没有过江东八千子弟。他曾手刃巴克斯,为多米尼克报仇,致身陷囹圄;如今,帕特里克和菲利普的死因终现天日,诺德斯却未能从三十五年来的自责中解脱,他仍背负着弑兄杀弟的十字架,仍心陷囹圄,岂是如麦克斯所言把子弹射向麦克斯就能得到救赎。
突然启动的垃圾粉碎车也缓缓前行,诺德斯回头,化名贝利的麦克斯故意让诺德斯看见自己消失在车后,诺德斯等车经过自己,看看车斗内的污秽垃圾,漠然地驻足原地,漠然地目送车前行,夜色雾霾渐渐聚拢,掩盖了车身,掩盖了麦克斯的再次消失。诺德斯此番未有伤悲,他不相信麦克斯这次的自我了断,但此番一别,生死无关,何况,三十五年前,滂沱大雨浇在派希、斜眼和“麦克斯”身上,也浇灭了他所有伯埙仲篪。
一辆满载时髦青年的敞篷车喧嚣而来,与诺德斯相错而过,车上一位年轻女郎鄙夷地把酒瓶扔向诺德斯,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,“滚!老家伙们,现在的世界不是你们的了!”
回溯细节,诺德斯和麦克斯在影片中有两次借潜水预演“消失”,一是贩私酒计谋成功,二人兴奋地在小船上手舞足蹈,不慎跌入水中,诺德斯先浮出水面,茫然无措地拍着水面呼喊麦克斯,二是四兄弟珠宝劫案后,黑吃黑枪战,诺德斯为麦克斯对自己有所隐瞒而生气,气氛缓和后借着上次落水的梗,把车直接开向栈桥,坠入水中,麦克斯先浮出水面,茫然无措地拍着水面呼喊诺德斯。
而命运轨迹的消失,究竟靠什么?好似常规的答案都是:性格决定命运、选择决定未来——诺德斯的胆量停滞在街头混混、地痞流氓,小富即安,他缺乏亡命之徒的那种无畏和强悍,他不想再听到多米尼克那句:“诺德斯,我滑到了!”,他以为监狱的生活已是最坏的极致,凭借本性和直觉拒绝了麦克斯的提议、选择告密,却看到兄弟们躺在冰冷的雨中,再也不会醒来。其后三十五年,诺德斯拖拽着“背叛者”的影子,烙印着“失败者”的标签,落魄潦倒,他的消失是被迫隐遁,在极度的悔恨与痛苦之下隐遁于自己的监狱中。反之,麦克斯的“消失”是主动选择,抛弃了多余的“负担”:派希、斜眼、肥摩、自己的名字、过往的生活,当然,还有诺德斯。重组了自己的利益合作伙伴,麦克斯的冷血是他成功的基石,这是在五兄弟打拼天下、积累原始资本时就逐渐积累起来的。他们这样的精英眼光高远,看得清所谓机遇,决断力强,“位高权重、美人归心”还只能算是低级成功的标准,麦克斯们翘首企盼的是金字塔顶端的荣华显贵,与梦想成功相比,“约为兄弟,则幸分我一杯羹”又怎么算得上薄情寡义?
从烟馆离开后的诺德斯,应该是在伊芙的温柔乡里逐渐恢复或者逐渐麻木,当他衣履齐整地回到俱乐部,却参演了一场兄弟阋墙的明争暗斗。卡罗尔如雌性动物一般挑选了麦克斯,被怂恿做些挑拨离间的丑态而不自知,派希和胖摩努力想粘合这行将破碎的兄弟情义,却事倍功半,斜眼摸出排箫,缓缓吹起《cockeyssong》,呜咽如泣。谁都明白价值观的分裂其实是信任危机,谁都在问自己,能做什么。麦克斯坐在自己添置的王位上暗自嘲笑诺德斯的痴情,也暗自谋划自己的将来。诺德斯努力镇定地啜饮咖啡,翻阅报纸,他隐隐觉得噩梦将袭,却无奈又无力,正如他的粗暴他的温柔都抵不过黛博拉的绝情,他莫名地恐惧即将到来的将来。
俱乐部时的排箫曲,只有短短几声。三十五年后,诺德斯找到兄弟们合葬的墓室,长长短短的排箫曲随着门开门合起起落落,时而悠远绵长,时而飘忽未定,似在倾诉离别,似在怀念过往——五兄弟一夜暴富后,精心打扮如纨绔阔少,志得意满穿街走巷,在车站行李寄存柜郑重地盟誓立约,离开前,镜头停顿几秒的是多米尼克贪恋的表情,还有他反复确认柜门锁紧的动作。回城时,五少年经过初建的曼哈顿大桥,背景中工业时代城市的蓬勃发展和少年们扬名立万的梦想相互交织,但场景的恢弘却对比着个人的渺小,水汽蒸腾弥漫,画面沉郁苍黄,已提前隐藏紧跟着的悲怆情节。
凄清幽邃的《cockeyssong》,在整部电影里怅盘桓而不能去,在俱乐部房间里回荡,在墓室里回荡,生离死别,一曲诉尽。
从街道来到烟馆,好似从江湖来到伊甸园。
少年的诺德斯躲在面粉仓库的隔壁,透过墙壁的砖缝偷窥黛博拉练习舞蹈,随着黛博拉裙裾飘动舞步回旋,空中轻轻飘荡一层薄雾,在光影和人影上都蒙上一层轻纱,乐曲悠扬,声声入耳,如斯伊人,翩若惊鸿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这是诺德斯曾经有过的伊甸园!
他始终不愿承认的是,当他被霸哥打伤,再也推不开黛博拉锁上的门时,他再也没有伊甸园了。
如果说少年时背着人阅读《马丁·伊登》,是一种让自己回归本真的方式。成年以后的诺德斯需要新的,或者说,成人的麻醉方式,麻醉自己暂时逃避或遗忘那些江湖恶事、那些由他自己制造的恶。他需要的是梦中的仙境,逃离彼岸的渡舟,而那诡谲的电话铃声,恰恰是把他拉回此岸的魔咒: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
影片并没有按时间顺序讲述,而是像常人的回忆一样跨越跳动,似乎很难理解最后一幕诺德斯的笑容,又似乎很容易理解:
诺德斯被麦克斯打晕,醒来发现其余仨弟兄已实施抢劫计划,与自己告密后埋伏下的警察正面交火,均中弹而亡。大雨如注,死生两隔,死神可知道内疚的滋味?诺德斯重回烟馆,只想麻醉自己,只想醒来时发现只是场噩梦,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重头再来过。
那无意识的笑容,实际上也是芸芸众生、等闲之辈的自嘲——白云苍狗,过眼云烟,很多追求或梦想,倾尽一生,谁都赢不了,但谁也输不起。
enjoyGUDIAN有温度,更要有深度